|
陈颐鼎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前,第八十七师正住防常熟附近,奉命闲扯运到上海地区参加战斗,一直打了三个月。于十一月中上旬撤退至镇江附近,一面整补,一面作人事上的调整,免去王敬久的兼任师长职务,专任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八十七师师长由副市长沈发藻升任。时该师辖有两个步兵旅,一个补充旅,后又将补充旅改为第二六零旅,合计为三旅六团,和炮、工、通信、运输、特务等营。我任该师第二六一旅旅长。十一月下旬镇江已是人心慌乱,市面店门紧闭。设在镇江的江苏省政府各机关,纷纷过江向扬州城迁徙,镇江城死一般的沉寂。有一天王敬久要我去见他,并交给我一份由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转来的蒋介石用红铅笔写给我的手令,派我兼任镇江警备司令,赶快就职,归驻龙潭副司令长官刘兴指挥。王敬久对我说:“这一任命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既是要你在镇江负责,那就将二六一旅留下,我带易安华、刘启雄两个旅先去南京接受任务,以后怎样办再说。” 自上海战场全面撤退后,国民党军接连丢失吴(恩苏州)福(山)线和锡(无锡)澄(江阴)线既设阵地,常州也相继陷敌。敌军分两路向镇江进犯(一路沿公路,一路沿铁路)。时我警备司令部尚未组织起来。十二月初,镇江外围战斗就打响了,以镇江南部竹林寺、鹤林寺等地战斗打得最为激烈,另有日军六辆坦克沿丹徒到镇江公路窜抵市中心,均被我军击退。 十二月六日,刘兴电话通知我说:“今晚有从贵州调来参展的第七师)番号记不清),开来镇江接替你的任务,你们交防后,回南京归还建制。”此时镇江外围阵地已形成犬牙胶着状态,整个阵地的调防已成为不可能,我只好命令部队相机交出阵地,然后自行到下蜀车站集合待命。我于六日夜十一时离开镇江先去下蜀车站等候部队。七日早晨,我在下蜀车站见有一列空火车见有一列空火车从南京方向开来,经询问乃知是师长沈发藻派来接部队的。师部命令我旅到尧化门站下车,尔后徒步行军到孝陵卫附近待命。 我部从镇江撤下后,即在下蜀开始车云,经过往返三次才将部队运完,这时已是七日近黄昏时分。在尧化门集中后,我们不行向指定地点集结。夜,很寂静。对一个刚离开战场的人来说,心情是轻松的。然而,我们所过村庄,到是倒塌的房屋,到处是断墙残垣,到处是刺鼻的焦烟味,没有鸡叫做,没有人迹。天亮后,上了京杭国道(宁杭公路),昔日孝陵卫的营房不见了,农科所的房子烧掉了,只有卫岗高坡上的孔祥熙公馆还是老样子。这一切又把人们带回战火弥漫的战场。 八日拂晓,全旅官兵约三千多人到达指定地点。鉴于在镇江连天战斗,加之由尧化门到集中地的一夜行军,官兵异常疲倦,乃令第五二一团在原中央体育场休息,第五二二团在钟灵街休息,旅部及其他配属单位,到孝陵卫休息,我偕参谋主任倪国鼎等人去城里找师长接受任务。不了走到中山门时,见城门紧闭,外面全用麻袋装土堆积,中间仅留一展望孔,城楼上三五个武装士兵头戴钢盔,左手臂上戴有黄底黑字的“卫戍”臂章,来回巡逻着。我们说明来意,要求进城,但他们坚决不许,并说非有长官部命令不许通过。我们只好退回卫岗,在孔祥熙公馆里架起无线电台向上级呼叫。 正当我们呼叫未通时,忽听部队休息方向响起枪声,我当时认为句容、汤山方面不会没有部队防守,可能出自与友军发生误会。正在猜疑中,忽见第五二一团私号长张某跑来报告,敌人已把第五二一团一个正在做饭的炊事兵抓走了,部队已展开,在体育场以西一带高地与敌人对恃着。我乃离开卫岗,在孝陵卫东侧高地用望远镜一看,当面队伍果真全是日军。遂将第五二二团展开在白骨坟、孩子里一线阵地,第五二一团后撤到遗族学校东侧一带高地,阻止敌人沿宁杭公路直扑中山门。时无线电台已与师部联系上,我即将我旅位置和目前情况以及打算向师部作了报告。师部复电统一我们的部署,并告知左右邻友军位置和战斗分界线后,再未有其他指示。 中山门外的战斗从此展开。这一天战况,从早到晚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地面炮火不断猛烈轰击中山门及其以南城墙,有一段被炸开缺口。敌地面部队不但向我白骨坟、工兵学校阵地进攻佯攻。大小五棵松村到紫金山东南麓一片树林,不知是谁放的火,火头顺着风向席卷般地由东向西蔓延,情况十分紧张。 九日天将破晓,我们发现小石山上空升起一个敌军观察气球,距地面约一千公尺,这是敌人利用它对紫金山以南地区到雨花台之间便于观察我方一切动态所谓。继而敌军以密集炮火向海福庵、工兵学校我阵地猛烈射击,另有地基多架配合乱反轰炸。大约三十多分钟火力袭击后,敌步兵约数百人以石家湾、大扬底、郭家底作进攻出发线,向工兵学校阵地冲击。由于这一阵地利用原有的永久工事构成强固闭锁堡垒,连连打退敌军多次冲击。从阵地前的敌尸中发现,进攻部队为日军第十六师团。当地军第三次进攻受挫后,我向上级建议,由孩子里经张家上向小石敌右侧背施行反击,结果以“万一出击不成,影响防守阵地兵力”为由,未被采纳,坐受敌人打击。 十日,南京城廓阵地经敌军两天时间狂轰滥炸,已有许多阵地被炸平,光华门两侧城墙被炮火击开两个缺口。午后敌军一部在坦克掩护下,突破了我右侧友军第二五九旅阵地,另一部约近百名在密集火力掩护下,突入光华门城门纵深约百公尺,占据沿街两侧房屋做据点,掩护后续部队扩大战国,情况很严重。上级命令第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和我一定要把突入之敌消灭掉,恢复原阵地,“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于是,我同易安华旅长商定,趁敌立足未稳,黄昏后开始行动,由他亲率一个加强团在通济门外向东北方向进攻侵入光华门之敌,我率两个加强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协同第二五九旅夹击突入光华门之敌背后,并阻止小石山附近敌人增援。经过八个多小时浴血奋战,终于将这股突入之敌全部歼灭。光华门内外横尸遍地,敌人遗有尸体五具有,皆为日军第九师团的。这场恶战,除许多建筑物毁于炮火之外,我第二五九理旅长易安华、我的参谋主任倪国鼎,另有两位营长和三十多名下级干部、战士都牺牲在这一反击战中。这是南京保卫战中最激烈的一仗,牺牲的人们应用为后人所怀念。 十二月十一日,正面之敌再次阻止了对我工兵学校阵地的争夺战,所有阵地前沿副防御设施,都被敌人炮火摧毁殆尽,而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天战斗的最大困难就是伤员送不出去。原因是占据老冰厂高地的敌人,以火力封锁了光华门交通;我守城门部队不同城外部队协调,将城门和昨天被敌炮火击开的两个缺口全部堵死。这样,不仅伤兵不能后送,且连城内外有线同化也就此中断,多次向上级要求改善,均未得到解决。更奇怪的是当地军对我阵地猛烈进攻时,中山门外路北我军炮兵阵地(部队番号已记不清)有普福斯山炮十二门,因怕敌炮火压制,拒绝我们的求援。 十二月十二日,我正面敌军活动情况较为沉寂,只听到雨花台方面枪炮声比较激烈,左翼紫金山有稀疏枪声,烧山的大火仍时断时续,我们同上级无线电联系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就中断了。入夜后,我派到左翼友军教导总队马威龙旅联络军官刘平回来说:“看有广东部队(恩后来了解为叶肇部队)很蒸汽地出太平门往东北方向去了,拒不答复去向。马旅行也许正往左边铁路方面靠去。”这时我在四方城指挥所了望城内有三处大火,黑烟冲天;九时许又有乌龙山要塞炮向中山门城内外盲目射击,有些炮弹竟落在我们阵地上;中山门到光华门一段城墙上已没有守军。根据情况分析,我认为占据必有变化。但守土有责,加上本师官兵在南京城先后驻扎多年,一草一木都具有浓厚感情,谁都有同南京共存亡的意愿,谁也没想到南京保卫战就这样糊里糊涂结束!我乃商之副旅长孙天放,带领少数武装士兵去左翼铁路线方面做实际情况了解。孙十三日零时左右自和平门骑着自行车回来,我才知南京已经不守,所有部队纷纷向下关撤去等情况。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右有老冰厂高地的敌人封锁了光华门去路;正面同敌人对恃着;后面就是护城河;只有向左往下关走一条路。以常理推论,南京城既是主动放弃不守,必会派出部队掩护大军转移,下关到浦口江面也会备有大量渡河器材,供给部队使用。我立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让大家共同负责撤离阵地责任,也特邀了第二六零旅旅长刘启雄、团长谢家询、蔡祺、参谋主任刘云五等人参加,并要他们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责。 十三日凌晨二时,我们开始从阵地上逐次撤退下来,派第五二一团第三营占领苜蓿园村到中山凹之线沿途阵地,阻止敌人跟踪追击,并要该营逐次撤退到下关车站附近归还建制。三时许,我们从中山门出发,沿中山门通往太平门城外公路,和玄武湖东侧过和平门公路撤往下关。路过吴王坟时,我特地去看了一下近两天来因作战被打伤腿脚而不能行动的数十名官兵,告知他们处于无奈,不能一块行走的苦心(自十一日起光华门被敌人火力封锁不能通行,我们即在吴王坟附近开设了临时裹伤收容所,利用团属输送连力量一个个往下关送,由于路远远送工具少未能及时送完)。据后来了解,这些官兵都被敌人惨杀了。每当想起这些为抗日流血牺牲的战士,内心无比沉重和内疚! 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在这五天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个指挥官因失职受处分。 我们自中山门集合地出发,便以急行军速度向下关车站奔去。沿途一片沉积,马路上的路灯照常亮着,玄武湖霓虹灯,仍象平日一样在一闪一闪地放光,唯有城内三处大火依然燃烧着,谁会想到这就是大屠杀的前夜呢?天刚朦朦亮,我们到达下关车站附近,随即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到处乱晃。健壮,我一颗因“擅自撤离阵地”而胆怯的心才放了下来。后又遇师部某副官,才知道王敬久和沈发藻等已在昨天下午过江去了,他是沈派来寻找师参谋长的。据他说,在煤炭港码头师部控有一艘渡轮,于是我带着部队向煤炭港奔去。 上午九时许,我们到煤炭港连个船影都没有盘间,只看到演讲一些流散的官兵,有的在绑扎各种各样的排筏;有的已漂在水中,随波逐流,顺江而下:也有人被浪打翻渡江器具而酷好求救的。我目睹这些情况已知渡江不可能,加之从下干到煤炭港路上部队已被人群冲散,我只得带着少数人沿江向燕子矶走去,想突破敌人保卫圈,在敌后村庄暂时躲避一下,再设法过江。午后三时许,我们已到了燕子矶。当我路过乌龙山时,还看到一些工人正在给永久工事浇水泥,我劝他们不用再浇了,他们反以不能耽误工期作答。我到燕子矶后,看到随我而来的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宪兵、警察和散兵,不下三千人。开始我很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因我身穿将级军官甲种呢军服大衣,所以他们把我当成高级指挥官,主动找我,要求跟我一起行动,听我指挥。我很作难,但又为这些力量的散失而可惜,更为有离群而走投无路的同感,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随即派跟我而来的旅部特务排十多人去山上警戒,告诫他们万不得已不许开枪,意在天黑后行动,旋将这些散兵集合起来编组部队。不了正在编组部队时,敌搜索部队同我派出的警戒部队打起来,而这些自愿听我指挥的人,一听到枪声,一窝蜂地四处逃去。 当时我身边只有两名卫士,一个副官和特务排长等七人,他们见敌人从占下往下追来,不由分说,把我连推带拥地拉到江边,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块二丈长六尺宽的木板,象是军队士兵床铺,放到水里硬要我上去过江。我看这块木板浮力不大,有心摸出手枪自杀了事,可是,身边的手枪早已被卫士们拿走,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这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宁死不做俘虏,我要大家都上木板,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木板离开江岸不到五十公尺,就逐渐下沉了,这些与我久共患难的战友为减轻木板上的重量,纷纷跳下水去,有的被江流冲击走狗而没有下落;有的则在江中大声喊叫:“我们有个旅长,谁能救他过江给他一千块钱!”由于他们纷纷跳入水中,木板早被蹬翻,成了斜立状态漂在江中。我掉到江里,手紧紧抓住木板一角,作最后挣扎。正在万般无奈之时,见身边漂来一个用六大捆芦苇扎成的浮排,上面有一人还放着一辆自行车。我请求搭救,他欣然将自行车掀入水中,拉起了我。他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是教导总队的上士看护班长。此时敌舰已在江面上横冲直闯,来往梭巡不已,并用机枪不断地对我利用各种漂浮器材顺流而下的官兵扫射,被打死或被敌舰装翻漂浮工具而淹死的人无法计数。眼看着战友们的尸体不断从我身边流过,江水被染红,情景凄惨,目不忍睹。更可恨敌舰上日军面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非但不自责,反而拍手称好,真是人愤慨万分! 十三日夜晚,我在马振海的帮助下,终于在八卦洲上了暗。上岸后,顿觉身冷肚饥,承一渔翁相助,我们吃了稀粥,换了湿一。十四日太阳已半竹竿高时,我们摸到下坝,听说上坝有红十字会收容护理,又赶往上坝,那里挤满了人,不下数千,很乱,谁也管不了谁。我在八卦洲待了两天,幸遇跟我多年的老卫士和其他一些占有。我们利用从上游漂来的木头、门板扎成排筏,于十六日拂晓,趁江上大雾,穿过敌舰封锁,渡过夹江,到达江北。后听说留在八卦洲的官兵,在江边被集中残杀了!这真是世界战史上罕见的残暴事件! 陈颐鼎:作者当时系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副 选自《南京保卫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 ||
| (来源:《南京保卫战》)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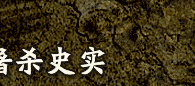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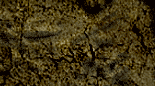 |
|
 |
 |
 |
 |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征集电话:(86)025-86612230 E-Mail:nj1213@vip.sina.com |
| 联合制作:新浪网 龙虎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