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占领滇西期间,在占领区内建立了约20多个慰安所,分别是:德宏潞西市芒市镇三棵树、树包塔佛寺、勐嘎、盈江新城大路边刀光如家、瑞丽畹町一道桥;龙陵的镇安街、董家沟、龙山卡、白塔、平嘎、腊勐;隆阳潞江乡的禾木树、芒岗等处;腾冲县城南门街熊龙家、黉学街孔子庙后宫、顺城街蔡家、南门外陈国珍家、明朗村荷花池村尹加令家、界头乡朱家寨朱诚明家、勐连街等处。另还有一些临时慰安所。如潞西允门村民的牛圈头上,畹町混板村下的战壕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滇西用作性奴隶的女性约有800名,其中500名是被日军抓来的滇西妇女。在这个万恶的制度下,有数千名滇西妇女被奸淫。 据潞西市公安局退休干警姜兴治回忆:解放初期他任公安员时,听目击者讲,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日军突然包围芒市的广姆、芒黑、等项3个村子,抓走了两车小卜哨(傣族姑娘),约七八十人。这些被抓姑娘,多数都有去无回。有一个返回家的,本来已向人述说了她的遭遇,被儿孙知道了,横加指责,以后她就缄口不语直到离开人世。 日军在芒市、畹町、遮放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不少慰安所。遮放慰安所开始时只有8个慰安妇,后来,又从广东拉来一批中国慰安妇。这样一来,日本慰安妇就成了军官的专属,而中国慰安妇就成了专供士兵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和工具。 芒市镇一小原来是一个寺院,内有树包塔景观。日军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慰安所。目击者告诉我们在日军占领期间,附近的住户常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女性的哭叫声。 在修筑芒市飞机场地下长廊时,日军强行拉走一些白天在工地上做活的疲惫不堪的傣族姑娘,将她们送到地下长廊日本小队长那里供日军玩弄。直到寨子里的坦范弄代表去求情才放回来。 1943年7月12日,住德宏勐嘎的日本宪兵队长中岛竟宣布:“年龄在16岁以上的女子,无论是否婚配与人,一经本部官兵选中,即应与本部官兵结婚。” 据德宏畹町芒满村老支书曼映回忆:日军侵占畹町时在一道桥(地名),当时靠山脚有一片草房曾是日军的军妓院,门口有日本兵站岗把守着,里面住着五六十个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过着暗无天日被糟蹋的悲惨生活。她们不得穿衣服,赤条条的,身上裹着一条军毯,见人就讨吃的。少女只有五六十人,可日本兵成百、几百地进去奸淫她们。天长日久,夜以继日,常常一天半天都下不了床。她们当中,又多是过了几个月就不见了,多半是折磨死了。过不多久,不知日本兵又从何处拉来一些新的少女供其继续玩乐。 混板村的曼相说:那时混板村下有一片开阔地,日本兵在那里横七竖八挖了一些战壕,战壕里的日本兵不知从那里拉来些小卜哨供他们玩乐。 腾冲光华街熊家当时曾设过慰安所,由10多个日军负责看守。日军将熊家和后面杨家的隔墙拆开打通,成了一个很宽绰的慰安所。据当时的目击者讲,日军排着队在大门外等候,每人拿着一个序号牌,叫到某号某号就进去。远征军收复腾冲时,日军将这里的几个慰安妇丢到井里淹死了。 日军看中了腾冲洞山村的尹老焕,扬言不将她送到驻地,就要杀光、烧光洞山。万般无奈,当地维持会只好将她打扮了送到日军驻地。在日军撤退时她回到洞山,成了一个木纳人。后来她嫁了一个憨丈夫。解放后一直由生产队作为五保户供养到去世。她连居民身份证都没有。死后,生产队让人一把火烧了她的简易住房,从此这个人就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她留给村人的记忆就是拖着鞋子,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步履缓慢地在村道上走过,不时地看上几眼跟在她后面向她吼叫“日本老焕”的不懂事的顽童们。 曾被日军抓到腾冲荷花池慰安所做饭的尹培荣老人回忆,当年荷花池慰安所有12个朝鲜慰安妇,日军又武力胁迫本村姑娘尹某某和邻村姑娘张某某到慰安所“慰安”江藤队长,致使两个姑娘怀了孕。第二年,江藤大队北上救援高黎贡山据点的日军,慰安妇随军转移,途中尹某某和张某某伺机逃跑。尹某某逃亡到缅甸,至今生死不明;张某某逃到勐蚌大山上,嫁给了那里的山民。 腾冲城里有一个叫蔡兰辉的姑娘,是下西街蔡兴国的女儿,模样俊美。她被日军“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田岛看中,成了田岛的专属,经常在一起达一年多,怀孕生了一男孩。中国远征军克复腾冲时,蔡兰辉母子和日军翻译白炳璜等人一起当了俘虏,后来在被押送往保山途中,把这个正在吃奶的男孩遗弃给了当地一个彭姓山民家,蔡兰辉从此就不知下落了。她的儿子后被山民养育成人,现在是腾冲城的一名小业主。提到当年他感慨万千。 有一位当年中国远征军的抗日老兵许国钧回忆说:“1944年9月14日早晨,我们攻进腾冲县城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尸体。在日军慰安所里,我亲眼看到有17个中国慰安妇和几个婴儿被日军刺死在那里,有一个慰安妇死了还紧紧的抱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婴儿,真是惨不忍睹!” 当年参战的日军吉野孝公在《腾越玉碎记》中,提到腾冲城被攻破前慰安妇的遭遇:吉野孝公和几个日军撤退时遇到了二三十个慰安妇,她们戴着钢盔穿着军服身姿显得很威武,但脸上却充满胆怯和恐怖,要求官兵们带她们走。其中一个还流着眼泪说道:士兵先生们,我有很多钱。说着卸下背着的袋子,抓出一大扎军票。当时军票已一文不值她却一无所知。还小心翼翼带在身上。最后她们还是被这几个官兵全部枪杀了。 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说:“敌寇去岁(1943)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该妇女等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 1944年9月26日的(《扫荡报》(该报纸的出版日期距腾冲光复后仅有12天),刊有战地记者潘世徵的一篇题为《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的报道: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敌人的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到了9月14日上午,国军克腾冲城最后一个据点,在防空洞里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她报告说,她是被日军抓来替慰安妇们打洗脸水的。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13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这篇报道还说:“又在一处城墙缝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她们都被蒙上了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潘世徵还报道说:中国远征军刚攻下腾冲城,他就在城南参观了几处慰安所。有的叫营妓公馆。一个院子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门上都贴着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这种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日本军医的名字、印章。慰安所房内的陈设,有如日本式家庭,大约是想造成“这里就是家乡”的气氛,以提高士兵的战斗情绪。日军为掩入耳目,给众多的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某某军妓院,或叫某某俱乐部,或叫某某娱乐部,或叫某某庄,如“翠明庄”、“清明庄”,等等。 日军占领龙陵不久,就让龙陵的维持会给他们供应600名“花姑娘”。因龙陵县城小,老百姓大都逃进深山去了,于是日军就组织大“扫荡”,四处搜寻“花姑娘”,搜到后先强奸又送到慰安所去长期供日军发泄兽欲。 日军第一四六联队进占龙陵平达后,立即包围该坝子的平达街子以及大寨、河尾、陈回寨等村镇,抓走二十几个年轻妇女当慰安妇。在街子赵殿试家开设了慰安所,后来又从别的地方拉来一些慰安妇,供日军发泄兽欲。据当地人回忆,隔几天,日军就要将一个当地较风骚的女人用滑竿抬到驻地供一个日军军官专门“享用”。后来这女人还生下一个儿子,这人一直被当地人称为“日本人”。 龙陵松山腊勐大丫口的一块山坡地上,设有一个为松山日本守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据目击者讲,这个慰安所是用竹子搭起的简单房子,里面用报纸糊起。一个慰安妇一小格,随时准备“犒劳”作战下来的日军。她们多是日本女性和朝鲜女性。皮肤很白,个子也挺高。 有个叫朴永心的韩国老人,当时就是被日军从她的祖国掠到这里当慰安妇的,并且怀了孕。身为孕妇的她,也毫不例外地每天要被日军无数次的蹂躏。2004年老人故地重游,到她曾被蹂躏过的腊勐大丫口慰安所遗址进行了指证。 滇西有许多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女性,但大都不肯站出来指证日军在滇西实施的野蛮的慰安妇制度。只有一人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因为她知道这不是她一人的灾难和耻辱,而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耻辱。她就是李连春老人。李连春是龙陵腊勐白泥塘人,日军占领她的家乡后,她在割、卖马草的途中,多次被日军强奸。出嫁后因失过身被丈夫家看不起而出逃,途中被日军抓到腊勐慰安所当了慰安妇。在慰安所,她一天要被几个或几十个日军蹂躏。她天天以泪洗面,每天吃一片药用以避孕,遇到接待不恭时还要挨领班的打。一天,一个日军在蹂躏她时兽性大发,在她的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她多次想逃跑,都因日军岗哨看管很严而未成功。约一年后,在慰安所打工的同胞帮助下,她才逃出虎口。笔者曾多次到她家看望和采访她。她因年老多病,记忆力已严重减退。2003年采访她时,她回忆起被日军咬的那个伤疤,并将它亮出来给我们看,至今还清晰可见。可惜这位深明大义、苦难深重的老人在2004年1月10日因脑溢血去世了。 就在李连春所在的腊勐慰安所里,还有二十多个中国慰安妇,大多数也是被日军用武力强拉去的当地妇女,还有15个朝鲜慰安妇(据说有的是中国东北人)和三四个缅甸妇女,此外还有几名日本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各人的结果不尽相同,但都是悲惨的。中国慰安妇则在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后不久多数被日军杀害了。有一个慰安妇是被用拐杖从嘴里塞进肚子杀害的。 龙陵县文史资料选集《松山作证》中记载:沦陷区妇女被敌人奸污的难以计数。难民村居住的杨从顺,先后被2个日兵奸污,后因争风吃醋,一天早晨被敌人枪杀在街子上。开饭馆的女人被敌人大白天搂抱玩耍。猛冒街子上居住的尹姓女人,怀孕7个月,在一个冷街天,突然来了20多个日军,将她轮奸到下身流血、胎儿堕地才停止。 当地汉奸黄召其为了献媚日军,答应带领日军去各山寨搜集100个女人来供其玩乐,后被马通译(复兴公司经理,留日8年,在潞江西岸被俘,被迫来龙陵沦陷区当翻译)将黄召基大骂一顿才取消了这回事。后来上面正式送来营妓(朝鲜、台湾姑娘),住在董家沟董、田两家。 驻腊勐松山的日军为发泄兽欲,到处寻找“花姑娘”,强暴奸淫糟蹋妇女。有的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其妻子,有的当着父母的面强奸其女儿,有的当着子女的面强奸他们的母亲。被这些日军强奸的妇女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有八九岁的幼女。有的被强奸、轮奸致死,有的被强奸后患上严重的妇科病,痛苦终生。 龙陵腊勐小水沟的李正维被一群日军抓住,用刺马指着他的胸膛,逼他去找“花姑娘”。李正维心想宁肯自己受罪,决不能将同胞姐妹送往虎口,他故意领着日军往没人的地方到处乱转,因找不到“花姑娘”,日军用刺刀一会儿割他的耳朵,一会儿戳他的身子,接连戳了十几刀。松山寨子一个16岁小姑娘李筛弟,一时疏忽被日军发现,立即被穷追不舍,小姑娘吓坏了,拼命跑,直至惊吓而死。当地一个70多岁的老人被日军强奸后,日军又强令一个20多岁的农民青年去奸污她,那青年坚决不肯,几个日军将他拖在老人身上,再用脚往青年的臀部用力蹬。 1997年4月的一个阴雨天,在龙陵县政协的帮助下,我们采访了龙陵白塔的一位张姓老太太。她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看到的日军在龙陵犯下的许多罪行。她因到慰安所做过活亲眼目睹了慰安所的很多事,但她一谈到自己是否被蹂躏一事,就用其他的话岔开去。与我们同行的留日研究生、国际慰安妇研究志愿者班忠义急得向她下跪,她都坚持说她自己没有受侮辱。她的难言之隐我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在潞江坝湾回族队,我们采访了80多岁高龄的马德沛老人。他向我们讲述了日军在潞江蒲满哨犯下的罪行。那时,日军一进村就挨家挨户搜找“花姑娘”。谁家不小心忘了藏女人的鞋,日军一看到就要追问“花姑娘”的下落。一天,日军进了他们村,他忙叫家里的女眷藏到后院去。他在前面与日军软缠硬磨,挨了日军的几个耳光,最后是送了几合红糖后才将日军打发走,保护了家里的女眷。但村头的母女两个(汉族)却遭了殃。妈妈叫刘招弟,女儿叫张丫头。日本人进村那天,有人听见她家传出阵阵惨叫,一夜灯光不灭。第二天看那两人都是眼睛红肿,肯定是被日本人糟蹋了。 潞江新寨线小德的母亲到碾房碾米时被日军轮奸,两个月都起不了床。隆阳区潞江芒岗也有一个慰安所。日军为方便席地而坐,特意将房主的桌子脚锯短。现在桌子还保留着。 隆阳区潞江禾木树是当年日军一个小队的驻地。日军抓当地的姑娘到他们驻地糟蹋。80多岁的张正孝老人说:(1942年日军占领潞江后),将妇女拿到营房玩弄是少数,多数是在路上、坡上脱了妇女的衣服玩弄。这些妇女活着的有,她们也有子孙,不好说,农村有忌讳。(日军)不管老少,上到60多岁,小到十多岁的都强奸。还叫中国男性跪着瞧,这事发生在刺竹窝。 据当时的文献记载:第七十一军特党部派往保山县属大塘子上江一带工作之宣抚队朱领队长昌洪返来称:遭日军蹂躏过之村庄满目凄凉,被其杀戮之妇孺尸体遍地皆是,惨不忍睹。宣抚队到后,即发动乡民收敛掩埋,免其暴露于地,臭气四扬。据调查统计:上江乡六保于今年正月间被敌掠去者逾21人,青年男子被杀害者23人,妇女被奸污者71人,房屋被焚者8村、39户、109间,牛马被劫去95匹,食米损失500石以上,谷子约2000石以上,财物损失约值国币29万余元。 日军当年建立的慰安所遗址还在,因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留下的后代被当地人称作“日本人”的还在,腾冲二战实物收藏家段生馗收藏的慰安妇们装化妆品的托盘、铜质脂粉盒、慰安妇们使用的茶具还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昭示着过去那个不堪回首的落后挨打、落后受欺凌的时代。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明的一种极其野蛮的法西斯制度,它对亚洲妇女的摧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慰安妇们没有错,即使是日本本国的慰安妇们,她们全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的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对于被侵略国家的妇女,则更是灾难深重。她们不仅要承受身体被躁躏的痛苦,还要承受被自己同胞歧视的心灵深处的痛苦。所以虽然时隔多年,也一定要为她们讨个公道和说法,以澄清事实真相,告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 ||
| (来源:)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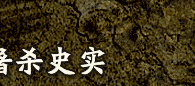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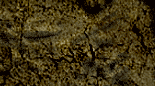 |
|
 |
 |
 |
 |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征集电话:(86)025-86612230 E-Mail:nj1213@vip.sina.com |
| 联合制作:新浪网 龙虎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