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  2005年3月13日,南京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将面临拆迁的命运。周围的老房子几乎被推倒,只有利济巷56号黄海霞的家还未搬走 图/中青在线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十余年致力于慰安妇研究,在海外机构的帮助下,他一直资助幸存的中国慰安妇老人。 澎淑 发自北京 苏智良真是很“平”的一个人:穿着平常、面部平和、语气平淡。 如果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项目、他正从事的事业,那么他与其他学者呈现给人的惟一不同就是拍照时很会摆姿势,更讲究背景色彩。 可是,有的人就像泡在杯中的接骨木花,在沉浸中香气慢慢散发,而且越发浓郁。 显然,苏智良就是这样的人。 1985年,祖籍浙江嵊州的苏智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他做研究生时写的论文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研究》。毕业后,他从事毒品史研究,写过《中国毒品史》、《禁毒全书》。 作为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他当初的研究方向是上海发展史。但现在,他更致力于调查中国慰安妇历史,寻找中国现存的慰安所,关注中国幸存的慰安妇的生活。 寻找慰安所 “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很矛盾。这个民族的特性也很矛盾。他们的民众很有礼貌,很爱学习,但是日本侵略过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慰安妇也是女性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刚刚结束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主办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与读者见面会的苏智良,口里边念叨时间太紧,要见缝插针,随即就步入了正题。 “从毒品到慰安妇,你研究跨度挺大的。” “对。我从1992年就对上海现存的慰安所进行寻找和调查,研究日本史算从那时起吧。” 1991年,苏智良作为上海师大选取的公派客座研究员在日学习深造。在这段时间,他还被安排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兼任日本东亚学院的中国语教师。 “涉入这个研究领域纯属偶然。” 苏智良边走边回忆。 1992年3月的一天,一个日本教授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问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 “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智良皱了下眉头。 在苏智良日后出版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里曾提及:一天,我在日本神保町的旧书店里,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黑白照片的上面,有着两排日本式的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去作乐。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与此同时,日本的《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经参与了慰安妇的征集。不久,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照片作为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象征,被各大新闻媒体报道采用,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 “我对这张照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杨家宅在上海的何处?里面的慰安妇是什么国家的女子?后来这个慰安所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1993年6月11日,苏智良结束了留学生涯,与妻子陈丽菲一起回到上海,一起投入对杨家宅慰安所“地毯似”的搜索中。 从寻杨家宅慰安所打头,到进“大一沙龙”、访“三好馆”,至今,他们已找到了149处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原址。 “大一沙龙”位于东宝兴路125弄,是日本海军在亚洲设立的特别慰安所之一,从1931年到1945年,它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我认为它不亚于‘奥斯维辛’。今年3月3日,我还去过那里,周围拆得差不多了,听说它已被列入拆迁计划,政府要在那儿建一个住宅商业区……” 苏智良双目扫向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稍时,他颇感无奈地笑笑。 寻找受害者 “我这次来北京,本想看望一个受害者,可惜时间不允许。她比较特殊,当年还是个女学生时,被一个日军高层看中,强占了好几年,并为他生了个小孩。即使她现在生活优越,即使那个日本人后来跑到中国向她下跪认错,她还是愤恨不已,她心里还是很痛苦。”车在拐弯时,苏智良看向窗外,突然聊起了“个案”。 “你好像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不动声色了?” “我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我家里存放着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每盘都是血泪交加,惨不忍闻。可能痛苦得都麻木了,也可能我是男性,感情坚强些,另外,我还有其他研究课题可以缓冲……” 停顿片刻后,“不,我还是痛苦的。” “她是南京的一个受害者。我们就叫她杨大娘吧。”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借“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为舞台举行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 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苏智良一行带着杨大娘前往大阪进行控诉。 “我记得很清楚。她不愿抛头露面,我们就用一块白布单子遮蔽着她,再把光打在上面,这样就可看到她的身形了。她在后面讲叙,旁边有人做翻译。当她讲到她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从那时到今天都在使用尿布时,我当场哭了……这种痛苦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 苏智良回忆着。 “你们是怎样找到幸存者的?” “有时是通过群众来信,有时是通过当地调查组的反映,有时是通过查阅老兵回忆录等资料。” 苏智良说。 他们为了找到这些慰安妇,会住在当地与她们沟通。有的人会很快袒露伤疤,有的人却死也不愿开口。 苏智良曾得知上海某处有一个慰安妇尚在人间,他们想了很多方法,老太太就是不承认。 “得知她有个幸福家庭,我特意请警察把她请到警局,就是为了避开她的家人邻里,但她不愿意回想。直到最后,她才悄悄地对我说,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就让它烂在我的肚子里吧。” 苏智良轻轻叹息。 苏智良是理解这些慰安妇的心理历程的。做过慰安妇的女子要么终生不嫁,要么嫁人后受到丈夫的毒打、子孙的欺凌。如果很幸运有个好家庭,她们就会过得和平常人一样。 “但伤疤一旦揭开,她们会加深痛苦。有的在讲述时会无法控制,号啕大哭。有的因此而患上精神病。每次问完后,她们都像死过去了。” 苏智良压低了声音,“我很感激我妻子,有些细节是要她去倾听的,有些情感交流是要她去做的,她比我更痛苦……” “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 “的确。否则张纯如不会自杀。但我们还要继续,也必须继续,我们必须记下来,让全人类都知道这段最悲惨的女性史。” 苏智良声音渐渐提高。 援助幸存慰安妇 “我一年要出去28次。两湖两广、北京、山西、吉林、辽宁、天津、山东都去过。有人问我为这事付出多少?精力无法计算,经济上以前没统计,现在大约有8万元是私人掏腰包。” 苏智良轻点着桌子,“我个人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想说的依然是幸存的慰安妇的生活问题。他到一个少数民族的陈姓慰安妇家里去,揭开她家的锅盖,发现里面竟是野菜。苏智良问她这是猪吃的吗?她告诉他,第一碗是自己吃,剩下的给猪吃。 “最惨的是山西的一个老人。”这位老人因为早年作过慰安妇而被村民遗弃,一个人没人照顾,昏倒在小道上几个小时醒来后,独自回家从水缸里舀瓢水喝就完事了。 “当地政府一点不管?” 苏智良没有直接回答,“有的老太太要出国控诉作证,当地官员就当着她们的面训斥道,你还干过这事啊?还想丢人丢到国外?回去,回去……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浙江义乌还不错。” 苏智良很想做一个系统调查工程,“现在不快点做,以后没有得做。你想想,这些受害者早年身体受过创伤,晚年境遇不妙,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可活多久?” 苏智良还曾想建所老人公寓,“国内没有慈善机关、基金会提供长期援助,所有捐款加起来才三四千。那些幸存者每人每月所得的100元补助,也来源于海外华人组织的援助。在韩国有慰安妇之家,在中国,有的慰安妇只想有口吃的就行。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经营,我就感到吃力。” “想过彻底放弃吗?” “想,特别是经费缺乏、人手不足的时候。但,只要有一个幸存者还活着,我们就会援助她到死为止。” 苏智良的回答依然平静,却极为笃定。 | ||
|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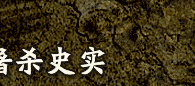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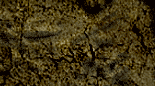 |
|
 |
 |
 |
 |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征集电话:(86)025-86612230 E-Mail:nj1213@vip.sina.com |
| 联合制作:新浪网 龙虎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